 0.4
0.4
 858.41KB
858.41KB
沒有什麼更奇怪地表明現代社會的巨大而沉默的邪惡。
沒有什麼比如今對“正統”一詞的非凡用途更奇怪地表明現代社會的巨大而沉默的邪惡。在過去的日子裡,異端是為了沒有異端而感到自豪。正是世界的王國,警察和法官是HERETICS 。他是東正教。他對反抗他們沒有自豪。他們反叛了他。軍隊以殘酷的安全,王臉的國王,酷刑的過程,合理的法律程序 - 所有這些都像綿羊一樣誤入歧途。該男子為正統而感到自豪,為正確而感到自豪。如果他獨自站在一個how叫的曠野中,那麼他比男人更重要。他是教堂。他是宇宙的中心。星星在他身邊搖擺。被遺忘的地獄撕裂的所有酷刑都無法使他承認他是異端的。但是一些現代短語使他誇口了。他笑著說:“我想我非常異端,”掌聲。 “異端”一詞不僅意味著不再是錯誤的;這實際上意味著頭腦清醒和勇敢。 “正統”一詞不僅不再意味著正確;這實際上意味著錯誤。所有這些都可能意味著一件事,只有一件事。這意味著人們不太在乎他們是否在哲學上是正確的。顯然,一個人應該在承認自己異端之前就承認自己瘋了。波西米亞人以紅色的領帶應該在他的正統上興奮。炸彈炸彈的動態器應該感覺到,無論他是什麼其他,至少他是東正教。
一般而言,哲學家通常是愚蠢的,要向史密斯菲爾德市場上的另一個哲學家著火,因為他們在宇宙理論中不同意。這是在中世紀的最後一次decade廢中經常完成的,並且在其對像中完全失敗了。但是,有一件事比為自己的哲學燃燒一個男人,這是無限荒謬和不切實際的。這是說他的哲學並不重要的習慣,這是在偉大的革命時期decade廢的20世紀普遍做的。一般理論無處不在。人類權利的學說被人類墮落的學說駁回。當今,無神論本身對我們來說太神學了。革命本身是一個系統。自由本身是一種約束。我們將沒有概括。伯納德·肖(Bernard Shaw)先生在一個完美的日報中透露了這一觀點:“黃金法則是沒有黃金法則。”我們越來越討論藝術,政治,文學中的細節。一個人對電車的看法很重要;他對Botticelli的看法很重要;他對所有事物的看法並不重要。他可能會翻身並探索一百萬個物體,但他一定找不到那個奇怪的物體,即宇宙。因為如果他這樣做,他將有一種宗教,並迷失。一切都很重要 - 除了一切。
 用戶還查看了
看全部
用戶還查看了
看全部
updated

update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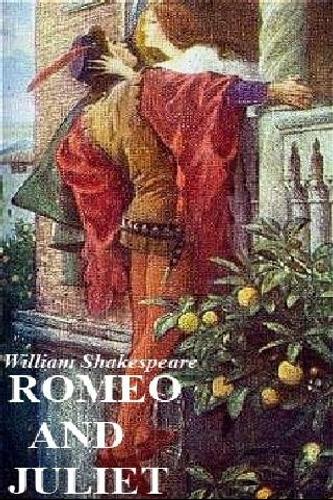
updated

updated

updated

update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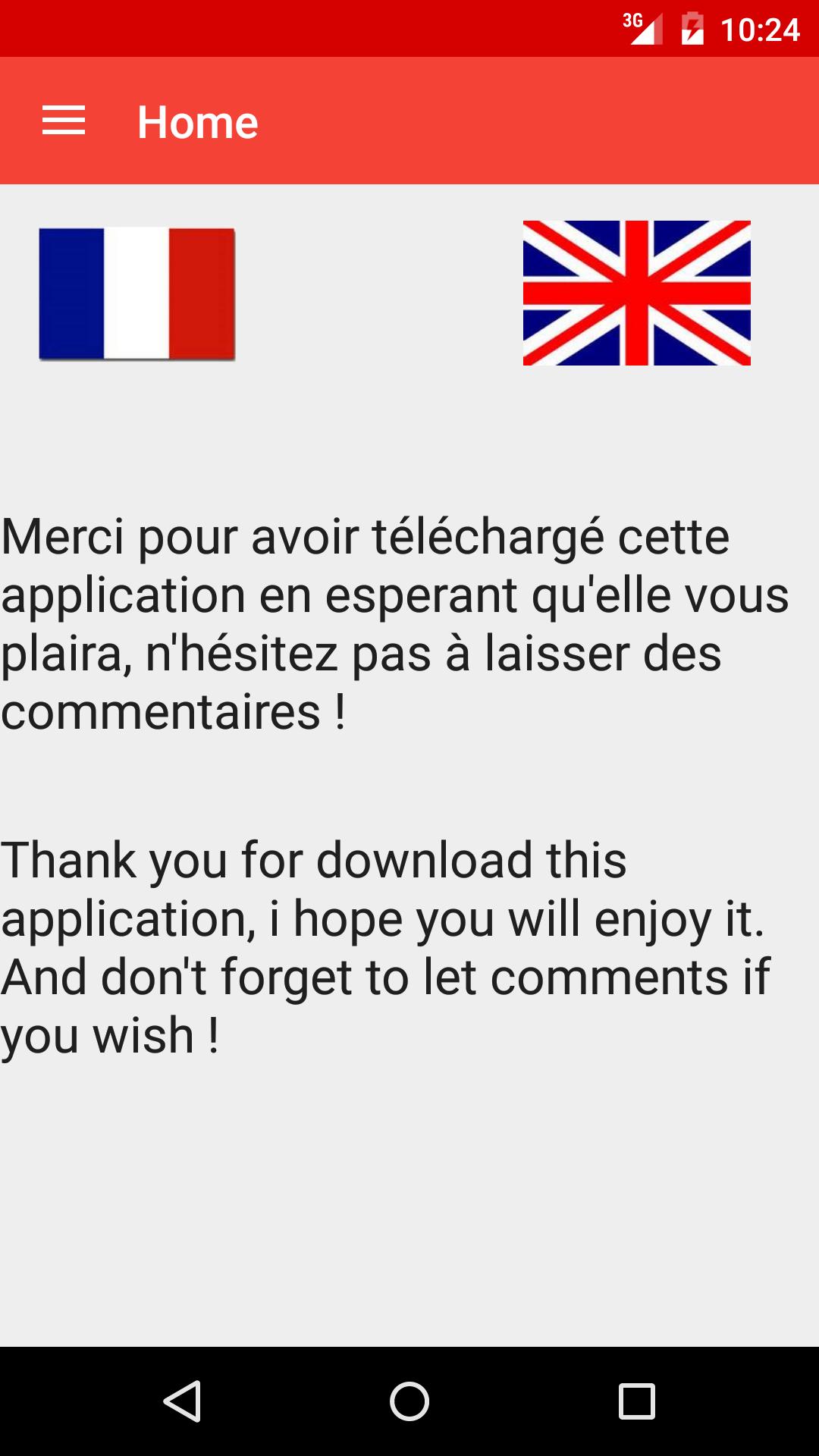
updated

update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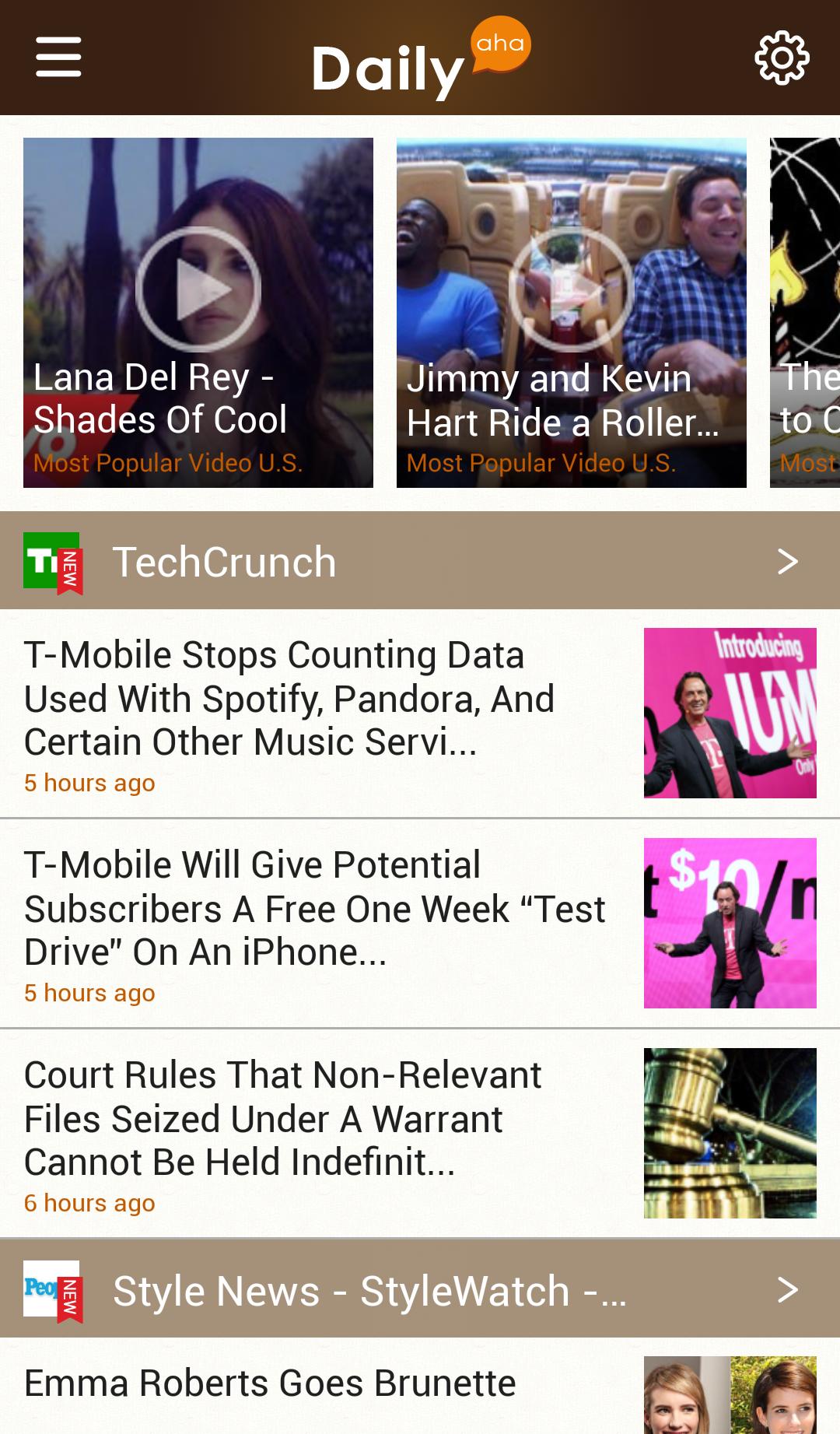
update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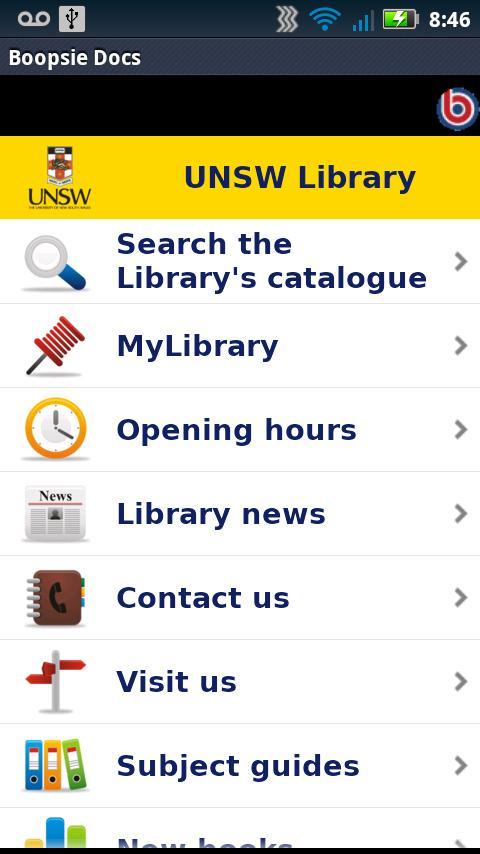
updated

updated

update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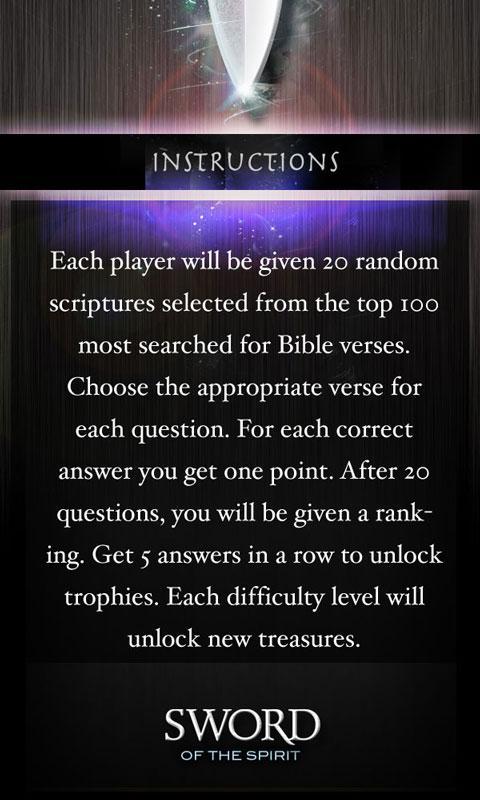
 熱門遊戲
看全部
熱門遊戲
看全部
updated

updated

update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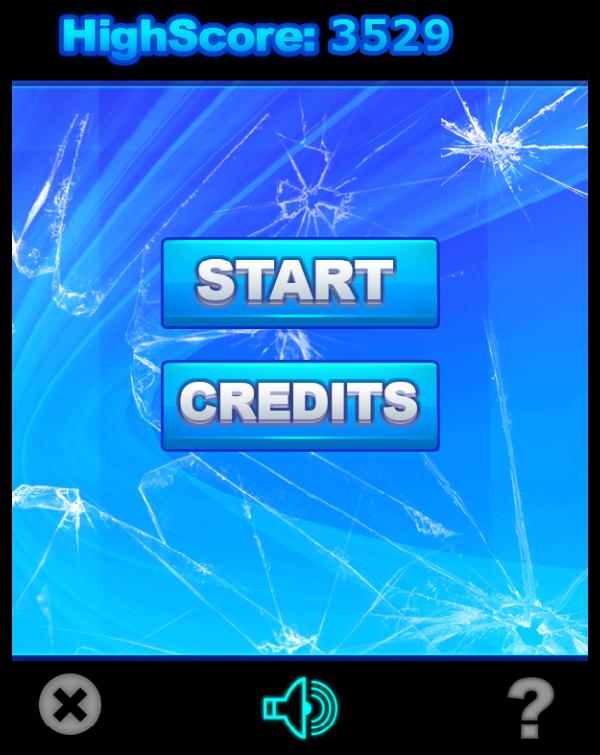
updated

updated

updated

updated

updated

updated

updated

updated

updated
